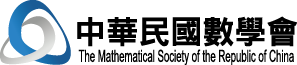電子報特選文章:人物專訪:蔡東和教授_2009.12.25
次閱讀
人物專訪:蔡東和教授_2009.12.25
清華大學數學系_蔡東和教授(98年度數學會學術獎得獎人),以下簡稱蔡
中華民國數學會秘書長_陳榮凱教授,以下簡稱陳
• 求學的經驗與研究心得之分享
陳:可否先跟我們談一下您求學的經過及心路歷程。
蔡:我先講我求學的經過,在數學的部分,我從小的數學就比別人好一些,像我在小學及國中的時候數學是班上數一數二的,國中還曾經拿過全校性的數學競賽獎,所以我一直覺得數學是很有趣的。然後我高中就讀於建國中學,班上的人都很聰明,我的數學也是比大部分的人好一點,但是我的物理跟化學就沒有像別人那麼的好,所以我高中的時候是數學跟英文比別人好。至於我大學為什麼選擇唸數學系,其實當時也沒有特別的理由,那時候填寫志願就是老老實實的照著填就是了。
陳:依照聯考志願排名填下來嗎?
蔡:對,我記得那時候臺大甲組有六個志願很有名,像是臺大化工、機械、電機、資訊、造船、土木等等。但是因為我高中物理跟化學的成績並不好,其中我覺得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當時老師教得不是很好,只有數學對我來說是比較容易讀,如果我數學聽不懂,回去還可以自己唸,可是物理、化學這種東西即使回去自己唸也是看不懂。後來因為聯考的時候沒有考得很理想,因此會去唸數學系並沒有特別的原因,就只是因為我的志願剛好排到了數學系而已。
陳:所以你在高中的時候,並沒有特別傾向於要往數學這領域發展?
蔡:我並沒有說一定要去唸數學,我那時考大學也是跟一般人一樣,從第一志願開始填起。後來去唸了數學系之後,現在想起來仍覺得是命中注定的樣子,因為我的分數再多一點點就變成成大電機系,分數再少一點點就變成淡江資訊之類的科系。我還記得我那時候聯考的分數是360幾分,總分裡面數學就佔了100分,這是因為當時我的數學考了80幾分,加上那時數學有加重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於是我的數學就變成總分100分了,所以我會去唸清華大學數學系算是很湊巧的機運。當然,我在清華大學唸書的時候,也遇到幾位對我影響甚遠的教授,我舉其中三位教授,例如沈昭亮、賴恆隆、林紹雄教授等等,這三位教授在教學方面皆是非常優秀的。
陳:所以林紹雄教授是先在清大,後來才去臺大?
蔡:他是先在清大,後來去交大,最後才去臺大。我在大三唸微分方程的時候是林紹雄教授教的,我記得我好像還被他當掉的樣子,因為我覺得他教得實在是太快了些,通常教的東西又比別人難一點,可是即便如此,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我很崇拜的人物之一,我對他的教學還是非常敬佩的。後來在我大四的時候,林紹雄教授就去交大教書了,所以我大學畢業之後就決定要去考交大研究所。我大學的成績其實不怎麼好,雖然有一陣子倒是還滿不錯的,不過後來有時候也是會常翹課,但是我對數學的興趣還是滿高的,只是我大學的時候對數學並沒有真的開竅、沒有真正進入數學領域的殿堂裡,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有在唸數學,實際上卻又沒有真正進入數學的狀況。後來直到我在交大唸研究所的時候,認真的程度遠比我在大學的時候多很多,所以我在研究所的兩年期間,研一修了一些林紹雄老師的微分方程,研二就跟著林紹雄老師做論文,他就是拿一些paper 給我看。其實在我研二那年的時候,林紹雄老師已經轉往臺大了,所以那個時候我每一個禮拜差不多都會去臺大一次,也因此我那時在臺大已經看過了一些人,比如陳樹杰、李瑩英、陳建隆等等。我覺得我在交大唸書的時候是相當孤單,畢竟以前的交大沒有像現在這麼地熱鬧,尤其放假時學校裡面都沒什麼人,大部份的時間我就自己留在學校唸書,所以在交大讀書的那段期間,我反而比較能夠進入數學的領域。說到跟林紹雄老師學習的部份,有好處跟壞處兩種,好處是他的學問相當地好,你不管向他提問什麼樣的問題,他都能很迅速的馬上就告訴你解答;壞處是他比較不會主動來鼓勵你,你跟著他學習是得不到太多鼓勵的話語,但是林紹雄老師那時對我還是相當的不錯,我們還是有常常聚在一起吃飯聊天。
陳:所以基本上,他的態度是不會特別鼓勵你往數學這方面去發展。
蔡:對,就是不會像其他老師那樣子特別鼓勵你,或是時常稱讚你的數學學得很好之類的話。可能會感覺他就是比較冷漠一點的,然而在數學領域這方面,他卻是毫不保留的,他有什麼東西全部都會教你。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他的態度是正確的,畢竟數學是一條很艱辛的路,不要輕易鼓勵別人往這方面發展。後來我碩士論文寫完之後就去當兵了,我總共在陸軍官校當了一年半的排長,當兵非常的累,從我一進官校那天開始就一直忙到我退伍為止,結果我的數學整個都忘了一大半。我當兵的時候有去申請國外的一些學校,一有空的時候我就唸托福、GRE,我記得第一年申請了十所學校左右,當時有兩所很不錯的學校給我入學許可,可惜沒有獎學金。我還請了林紹雄、阮希石兩位教授幫我寫推薦信,他們都幫我寫得很好,我很感謝他們。另外再加上我在交大是第一名畢業的,所以申請到的學校都還算不錯。只可惜當時的我沒有足夠的錢,家裡的經濟狀況又不允許我自費去國外唸書,所以我選擇在當完兵之後先回交大當了一年的講師,一個學期負責教兩門微積分課程,一方面也讓自己再多唸些數學的東西。最後,我又重新再申請國外的學校,因為我已經決定要出國。其實那時也搞不清楚為什麼一定要出國唸書?我在想,可能只是因為那個時候大部份的人都出國唸書吧。
陳:就覺得出國唸書是一條很必然的道路。
蔡:對,我們班到現在還有六、七個人還在美國,我記得我們班畢業後如果沒有馬上出國的,幾乎畢業後都陸陸續續在工作之後又出國去深造了,我想這種情況在臺大應該會更多吧。而且事實上我在交大當一年講師也沒存到多少錢,所以如果我要出國唸書的話,就一定要拿到獎學金才行,於是我就把申請學校的level 往下降一點,這樣子比較有機會申請到學校的獎學金,我申請到的州立大學包括俄亥俄州大學、普渡大學等等。我第一年就去了普渡大學,現在我回想起來仍然覺得很辛苦,我在那裡修了三門課程程,代數是王叔平老師教的,他是你們臺大數學系的校友。我印象很深刻,他每個星期都要我們交三次作業,我們學生幾乎每天都在寫作業,星期一的作業星期三要交、星期三的作業星期五要交、星期五的作業下周一又要交,所以我的印象是一天到晚一直在寫代數作業,這讓我覺得我們在國外唸書的壓力是遠遠超過在國內唸書的。
陳:沒錯,國外整個唸書的步調都是很快的。
蔡:他們步調真的很快。接著我轉去了明尼蘇達大學念書也是一樣,步調也還是非常的快,每天一早起來就一直忙,忙到你晚上睡覺為止。
陳:就差不多每天都是在寫作業這樣子。
蔡:對,我在明尼蘇達大學也是這樣,雖然感覺上是比普渡大學稍微好一點,但每天還是一樣很忙碌。我在普渡大學的時候,一開始也沒有想到要轉校,是因為後來有一次打電話給林紹雄老師,他剛好在明尼蘇達大學訪問,當時他問我要不要轉校,原因是那時候我跟他說普渡大學沒有太多人在做微分方程這方面的東西,所以就突然興起想要轉校的念頭,剛好我那時候也想要進入更有名的學校。結果有兩所學校願意給我獎學金,其中因為明尼蘇達大學的方程明顯的比另一所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好,我思考了很久,最後便決定選擇去明尼蘇達大學就讀。明尼蘇達大學的資格考非常難考,還好當時我一次就考過了,接著我第一年又再唸了一年的代數,因為我代數比較不好,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在代數上面。雖然說我之前在普渡大學有跟王叔平老師學過代數,不過普渡大學教的代數level比較淺,明尼蘇達大學的代數level相對的高很多,所以我去到明尼蘇達大學的第一年,就又重新唸了很多代數的東西。幸好後來在考資格考的時候,我一看到試卷就知道我一定會通過,因為裡面總共十題的題目我就有七題會寫,不過事實上也只有那七題會寫,另外的三題依然寫不出來。考完代數之後,我跑去唸動力系統,是跟力學有關的部分,因為那時我跟林紹雄老師學習數理古典力學,我第一年的指導教授是採取放牛吃草的方式,他是不大管學生的。接下來我在明尼蘇達第三年,我就跟Ben Chow學幾何、PDE。因為我以前唸過動力系統,有一些幾何的基礎,再加上我又有跟林紹雄老師唸過一點點PDE,在我幾經考慮之下,第三年決定開始跟Ben Chow學習。我在那裡總共唸了七年,不過那時候唸七年沒什麼大不了,因為當時博士班的平均修業年限是唸六點八年。當我唸到第六年的時候,我就知道我應該可以畢業了,可是因為有些paper還沒弄完,所以到第七年才畢業。我在第七年畢業時已經有跟Ben Chow合寫一些論文,包括有一篇是我自己寫的論文,我們合寫的四篇論文都已經在1996年發表,而我在1995年的時候就已經確定我可以畢業了,因為那些paper在1995年都已經確定被接受了。畢業後,我在美國有一個面試機會,是在邁阿密的南方、佛羅里達的一所學校,那個學校雖然是屬於州政府的大學,但基本上跟野雞大學差不多,那裡有很多西班牙裔、巴西或是墨西哥人,我覺得那個地方不是很好,所以我也考慮了很久,我那時候找工作真的很困難。
陳:這樣聽起來,你那時候的狀況若是以現在來看的話,事實上應該還是有很多機會的。
蔡:可是當時我們找工作需要申請到一百多所學校,那個時候還有一點對我們臺灣人雪上加霜的是,剛好碰上了中國大陸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很多大陸的留學生都擁有綠卡,他們找工作都遠比我們臺灣學生來得吃香、順利一點,這其實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他們有綠卡。我工作找得不是很順利,申請MSRI也是在waiting list裡面,事實上在waiting list裡面的話,表示跟「沒有」是差不多的。
陳:對,因為前面的人不太可能會放棄。
蔡:沒錯,我記得類似博士後這類型的工作,大概都會有800人申請,所以我在1996年找工作的時候真的是很困難。大致上來說,我求學的過程總共在新竹待了七年,大學四年、交大兩年以及當一年的講師;後來去美國普渡大學唸了一年、明尼蘇達大學唸了七年。我回臺灣之後,先到中正大學教書,我其實還滿懷念在中正的那段期間,因為我覺得中正的環境比較單純、沒有太多外界的干擾,我是指研究環境這方面,不曉得你贊不贊成?
陳:我覺得在那邊可以很專心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跟研究。
蔡:另外我覺得中正有一個優點就是,因為他會給你某種程度的壓力,讓你一定要發表論文。
陳:那個時候助理教授應該是有七年還是八年,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在你一進去之後他們會給你兩年或是幾年觀察的期限。
蔡:沒錯,他們會給你一個期限,並且要求你在這個期限內要有些成果出來。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這個要求不會太嚴格,而且這還會有push你做研究的動力跟壓力。
陳:尤其是一開始的前幾年,把習慣建立之後,這會是未來的助力。
蔡:對,以後就可以繼續養成這種習慣。我是覺得剛畢業後的前五年是關鍵時刻,尤其是博士班剛畢業後的五年內,如果這五年都還有在做研究的話,那麼大概就比較會持續下去;但是如果這五年內沒有做出任何東西,那麼可能以後就不大容易繼續做下去了。我在中正期間最相關的人就是林長壽老師,在回中正之前有跟林長壽老師通過幾次電話,當然也有跟余文卿老師通過電話,我那時候沒有去清華大學而是去中正大學,這或多或少都跟林長壽老師有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以前我去臺大的時候,那時臺大都是兩位老師共同使用一間辦公室。當時是林紹雄與黃武雄老師在同一間辦公室,後來變成林紹雄、林長壽老師同一個辦公室,每當我去臺大找林紹雄老師之時,便常常會遇到林長壽老師,因此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就已經認識了林長壽老師。加上林長壽老師又認識Ben Chow,所以在這些因素之下,我就沒有去清華大學了。不過事實上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那時候我有先去看一下中正跟清華的環境,由於我們在美國待了很多年的時間,覺得中正四周都是稻田跟甘蔗田,環境跟美國比較相像;我後來又跟我太太去新竹看了一下,那天剛好天空下著毛毛細雨,馬路上又都是塞車的景象,所以我太太就說不要來新竹,最後我就決定選擇去中正大學了。至於我選擇去中正的原因,林長壽老師有某些部分對我是有影響的,他對於數學這方面有著極大的研究熱忱。
陳:這點是大家都同意的。
蔡:對,我們都同意這麼說。他會到辦公室跟我們說他昨晚唸書唸到多晚之類的,我覺得以對做數學研究來說的話,要找到一個像他這樣對數學這麼有熱忱且專注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後來幾年之後又基於某些因素,我便離開了中正,但這並不是因為我覺得中正不好的關係,我到現在仍覺得中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這部份是因為我的小孩也慢慢在長大,會覺得說鄉下地區難免會有某些不足的地方。
陳:還是會有某些侷限。
蔡:對,所以後來再加上我偶爾來清華大學的時候,有一些老師會問我說要不要回來清華這樣子,尤其我特別感激已過世的呂輝雄老師,他一直鼓勵我再回來教書,所以我在中正待了七年之後,我就決定再申請回來清華大學。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我回來清華大學已經又過了六年的時間了。我想這基本上就是我整個求學的過程。
• 在臺灣做學術研究的感想
陳:可否再跟我們談談,關於你在臺灣做學術研究的過程與所遇到的問題。
蔡:做研究方面的話,我1996年一畢業就回來臺灣了,我回來臺灣工作之後的兩年,還有跟Ben Chow合作,在1997年、1998年跟Ben Chow合作寫了兩篇論文,不過我在美國的時候差不多都已經知道這兩篇論文要寫什麼了。
陳:所以在你回來臺灣之前就已經知道了 。
蔡:對,只不過我回來臺灣之後就很忙碌,彷彿又回到了交大孤單的情景,我基本上從2000年到2005年都是自己一個人在做研究,自2006年到現在有一些是和我的博士生合作,從2006年到2009年這段期間差不多有5篇論文,其中也有跟幾位老師合寫的部份。我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在於跟我同行的人太少,沒什麼人跟我做同一個領域,反倒是在明尼蘇達大學的話,就有很多人在做方程,他們的PDE seminar都會有很多老師跟學生去參與。
陳:他們的團隊是很大的。
蔡:然後又再加上有很多學生共同的參與,那種感覺就會覺得很熱鬧。
陳:會覺得旁邊的人都在做這種東西。
蔡:對,所以覺得自己不做是不行的,因為大家都在做,那整個氣氛是不一樣的,但是回到臺灣之後就又變成自己一個人做研究,雖然說現在的E-mail很方便,但是我覺得有些時候做研究只光靠E-mail還是挺麻煩的,我認為學數學最好的方法還是能夠讓大家聚在一起面對面、互相討論。除了同行的人太少之外,另外一點是,我覺得現在博士生的程度並不是那麼的好,當然我的學生林育竹她是真的非常的用功,可是一般學生的話我覺得就不是那麼地用功。
陳:現在整個風氣不是那麼好。
蔡:對,我覺得博士生的英文程度也不是很好,也不大去聽演講,即使聽演講之後也不怎麼敢提出問題,他們不太敢發問就是了,跟老師之間的互動也不是那麼密切,現在博士生這個樣子跟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的感覺實在是差很多。
陳:聽演講這些事情在國外都是天經地義、很正常的事情。
蔡:沒錯,可是感覺在國內的話,好像就要拜託他們來聽演講,我不知道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在哪些環節出了問題?舉例來說:我在國外當助教的時候,辦公室外面常常排了四、五個學生等著要進來問我數學問題,但是當我回到臺灣之後,我的辦公室一整個學期卻完全沒有學生來問我問題,不知道陳榮凱你覺得如何?
陳:我想會不會是跟他們的學費昂貴有關係?
蔡: 這個也許也是有關係的。
陳:學生會想到每天都要花很多錢到學校上課,因此基本上就不會想要浪費這些學費,也許平均每天都要花到美金一百多元左右,所以相對之下就比較認真來問課業上的問題。
蔡:總之,我覺得在國外不管是聽演講或是問問題等等,全場都是很熱鬧、很多人參與的。可是在國內的話就少很多,我不曉得這在臺大的情況是怎麼樣?不過因為臺大學生的人數比較多、素質也比較優秀,所以我想這種情況可能會好一些吧。
陳:臺大的情況相對的是有好一點,可是相較於國外的話,一樣還是沒達到我們心目中期望的那個標準。
蔡:我在美國總共待了兩個學校,普渡大學跟明尼蘇達大學,這兩個學校給我的感覺都差不多,普渡大學的方程給我的感覺不是那麼強,但是只要有演講活動,我們博士生都一定會去聽,並且還有很多學生都會非常踴躍的提出問題,那種感覺就好像菜市場一樣地熱鬧,反觀我們國內的學生就不大會這樣踴躍。我真的覺得博士班學生應該要多去參加一些活動,多去聽聽演講。因為目前臺灣數學界的活動遠比我們那個年代多了許多,比如像是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的活動等等。
陳:可是一般學生常常會說他們去聽演講的時候都聽不懂。
蔡:我覺得這個倒是無所謂,因為很多東西有時候聽不懂是正常的。就以我自己來說,我聽了很多的演講,算一算差不多也有一、二千多場左右,光是以我在普渡大學一年、明尼蘇達大學七年來計算,總共就有八年的時間。尤其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的時候,平均一個星期至少要去聽一、兩場演講,若再加上有些時候有大型的演講,一天之中就會有五場,那麼一年有五十二個星期,一年下來就有一百場,八年下來就有八百場之多,除此之外,再加上回臺灣又聽了很多場演講。我認為聽演講就是這樣,大部份都是聽不懂的,但是偶爾還是會聽到別人做的問題跟你的想法是很接近的時候;或者說有些東西你在心中是這樣認為,然後過了十分鐘之後,當他說出了跟你一樣的看法時,你會覺得很欣慰,因為那個時候你會覺得自己的想法是沒有錯的,有人也跟你一樣有著相同的看法。我不知道別的領域是怎麼樣,我們方程的東西是當你只要演講聽多了之後,你就會知道做這研究的手法是如何了,所以我覺得聽不聽得懂這種東西沒有很重要,因為你很難聽到一個演講跟你自己研究的東西一模一樣,可是你可以透過這些來培養你的研究技巧跟常識。
陳:聽演講可以聽到跟你相似的、或是相關的資訊,這些對我們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蔡:對,我覺得這些東西對我們很有助益,所以聽演講基本上是可以學到在課本上所學不到的一面。聽演講真的是很重要,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去聽演講好像是很浪費時間的樣子。
陳:可是很多時候學者們的一些想法、理念,都是沒有辦法寫在文章上的。
蔡:對,沒錯。坦白說有時候書上看到的論文也不見得寫得很好,因為很多真正重要的想法是不可能寫成文章、也不可能寫在論文裡面的,要不然每一篇論文不就上百頁了。所以很多時候都是你必須自己多去聽演講,才能有辦法去聽到人家心中真正的想法、看法、或是對方程的感覺等等,這些東西唯有自己親身去體驗才會曉得。
陳:因為這種東西在基本上是完全不會寫出來的,也不可能會出現在教科書上面,而且更不會一字一句、且完整地敘述出來說因為當初覺得怎麼樣,所以後來怎麼樣之類的說明。
蔡:所以這種經驗是十分珍貴的,就好像是一個年紀很大的人在跟你分享他的人生經驗一樣。另外,聽演講的好處是,你還可以當場提出問題。有些東西你如果覺得說某個方程跟你的研究有一點點關係的時候,你可以問他相關的問題、問他的看法是怎麼樣,他通常可以馬上回答你,這些對你同樣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我覺得反正既然有一個人在那裡可以讓你免費問問題,那麼why not?不妨就多問看看吧。當然有時候也會聽到很不好的演講,這情形當然也是會遇到,但我覺得也無所謂,反正就做自己的事情也是可以的。我覺得博士生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不敢提出疑問,他們應該是害怕自己所提的問題不對、或是害怕被人家取笑等等,我認為這是需要克服障礙的。而當我自己去聽演講的時候,我也經常會在提問一些問題之後,才發覺為什麼我要問這種笨的問題,當下我也會覺得很不好意思,但我真的覺得其實無所謂,假如你得到的答覆能夠解決你的問題的話,那種感覺真的是會很棒。反正數學這個領域就是這樣,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你的態度也需要open一點才會比較好。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的時候,就遇到一個學生,他一開始什麼都不會、都不懂,我們東方人有些還會嘲笑他怎麼連最基本的問題也不懂,但是我覺得這真的沒關係,他不懂的地方就一直提問,今天不懂、明天不懂,最後總有一天他就會全部都懂了,甚至也許可能就變成專家了。後來我聽說他就跑去德州奧斯汀大學了,研究做得還不錯呢。這是美國人的長處,他們即使不懂也很敢問問題,態度是比較open的,再加上美國人做研究的行事風格跟我們東方人很不一樣,他們能夠很快就進入狀況,但是我們的博士生在這方面就需要多多加強一下。
陳:現在的博士生會不會對他們以後的未來有自我的限制,他們通常並不會覺得自己以後會成為偉大數學家之類的,反而是覺得說到時候只要在國內找一個教職工作就好了,而不是說像美國的學生一樣,都會想像自己有一天也能夠成為偉大的數學家。
蔡: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個人心態的問題。國內的博士生即使是在國內唸博士學位,但還是可以繼續利用「千里馬」的機會去國外待上一年或是兩年的時間,現在這種機會也滿多的,所以我覺得先不要限制自己太多,很多事情都是事在人為,不要總是認為自己只是小咖,一定要先把眼光放遠,有時候在你把眼光放遠之後,有一天便會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回報。
• 對目前臺灣數學界的發展有什麼建議與期許
陳:請再跟我們談談對國內數學界的建議、期許或是批評。
蔡:批評的方面,有些事情的確是需要改進的,首先第一點就是我們大家的薪水都一樣的問題,會覺得說這個部份是一個很不公平的問題,但是這個又是很難解決的問題。我們知道在國外的薪水是不一樣的,我知道有些人的薪水很高,甚至是別人的兩倍;然而在我們國內,有一個相當不好的地方是大家薪水都一樣,那麼有時候就會覺得我做那麼辛苦幹嘛?即使是我,我有時候也會這麼覺得。當然現在因為有五年五百億的補助,所以薪水可能會有一些些小差距,但是這差距又很小、很不明顯。
陳:對,這樣的差距很小。
蔡:一般來說,我們大學教授的薪水是十萬元,但是在國外的話,差異可以高到三十萬之多。對我們國內來說,我知道要打破這個瓶頸是不容易的,但是這是一個很明確的缺點,不曉得你的看法如何?
陳:這基本上我覺得會造成一種反淘汰的現象。
蔡:對,這會變成說隨便你怎麼鬼混,你的薪水都跟大家一樣多,這是很不公平的。另外一個不好的地方,大部份的學校都沒有淘汰的制度,年輕人的壓力又不夠大,好像一旦進入一個學校之後就是等待。
陳:像是進入學校之後就在等退休的樣子。
蔡:沒錯,等養老退休的樣子。
陳:通常在你找到一個工作之後,主要需要做的事情是可以非常少的,你只要每個星期固定教完多少書就可以。
蔡:假如你真的要這樣子混的話,其實人家也拿你沒辦法,每個禮拜來教個幾門課,其它事情你都不管,當然,你要不要這樣子是你個人職業道德的問題,這在法律上是沒有限制,我想每個系上都會有這種人,這也是不太公平的,他領的薪水跟你領的也差不多,所以我想我們給年輕人的壓力不夠大,這是我覺得還不夠好的地方,至少我們可以像中正那樣給一些壓力。
陳:留幾年的觀察期。
蔡:對,給年輕人幾年的觀察期,我覺得中正這樣很不錯。因為有些壓力總是好的。另外,我覺得可以考慮如果說你的研究做不動的話,那麼你就把教學給弄得好一點也是不錯的,當然這個問題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陳:或者是說評鑑的方式可以採用雙軌制來訂標準。
蔡:如果說教學弄得好一點的話,讓學生覺得這個老師上課教得又好、內容又吸引人,讓學生會來想唸數學,這個樣子也是不錯的,比如說像是林紹雄老師,我覺得他就是這個例子的典範。
陳:那麼你覺得現在跟十年前有哪些差異?
蔡:我覺得優秀的年輕數學家人數比例,跟十年前比起來多很多,我們系上這幾年的年輕教師如陳俊成、陳國璋、何南國、鄭志豪等等,他們都相當地不錯,我想臺大應該也有很多優秀的年輕教師,所以感覺上我們國內數學界十年前比較有activities的只有中正,當然別的學校可能不這麼認為,但是至少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陳:我覺得那個時候的中正另一個長處是那個時候的年齡層是比較低的、大家都比較年輕的。
蔡:現在十年後的話,因為有數學中心、理論中心的成立,數學界多了很多的活動來源。有時候我也覺得這也是個人見仁見智的問題,覺得國內的研討會是不是太多了一點?常常一下子有這個研討會、有那個研討會、又有年會、什麼會的,我自己的習慣是因為我平常就很忙,所以我通常不大喜歡給talk,畢竟我認為給talk的話是需要很多時間做準備,而且我沒辦法像其他人一樣,這個talk也給,那個talk也給,這對我來說是沒辦法的。
陳:我覺得我們這些活動基本上還是我們自己的人比較多,因為國外seminar的speaker都是由外國來的。
蔡:對,國外seminar的speaker都是由外面來的,而且有時候有些的speaker都還是很大牌的。像是林芳華教授已經是夠大牌了,而他也是來只給一個seminar talk。不過有些問題都是先天的,因為同一個領域在國內都是自己在做,如果有兩個人一起做的話就已經算是非常不錯了,不過大部份都是你自己一個人在做這東西,像我跟褚孫錦,雖然是同一個領域但是都還是自己一個人在做。這是先天的不良,我們沒有辦法達到的規模。
陳:所以這個先天指的是規模的問題。
蔡:對,我們沒辦法達到那樣大的規模,但是我覺得至少最起碼要有三個人左右。
陳:但這我不完全同意,因為像是荷蘭或是比利時這樣大小的國家,他們人口數不見得比我們多。
蔡:對,他們人口數少,或者可能還是有別的因素。
陳:或者是我們現在整個數學界的active的人的比例需要再高一點,這樣可能就會有一點改善。
蔡:清華很難界定,有些老師其實有在做研究,但是他們的曝光率也不高,但是事實上他們也都有在做研究。
陳:這種可能就要歸類於不active的。
蔡:另外我覺得是這樣子,其實我們國內數學界存在不少人,他們對於理論中心的看法跟別人有很大的不一樣,他們雖然沒有很明白的說,但是他們卻是認為自己關起門來就可以做數學研究了,也有不少人是這個樣子的。所以某些老師就會覺得說他們沒必要去跟理論中心有太多的接觸,但是他們有沒有在做研究?有的,他們還是有在做研究。而且有些老師他們的研究其實還做得不錯。不過我還是覺得學術這種東西,在某些方面還是要適當地跟外界活動多接觸才行,因為你要吸引學生來學習,適當的活動是有正面的效果,不能說完全關起門來自己一個人做研究。
陳:所以你認為敬業的態度跟比例高一點都還是好的。
蔡:沒錯,敬業的比例高一些還是比較好的。
陳:那麼我們今天的訪談就進行到這裡,謝謝蔡老師接受我們的專訪。
蔡:謝謝大家。